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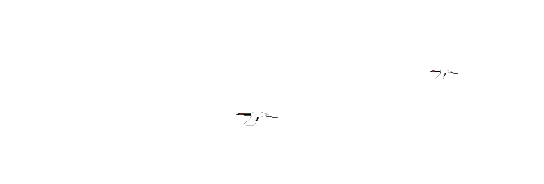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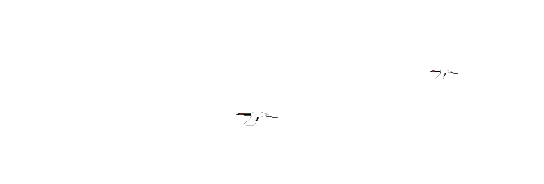
外祖父姓周,名金石。从爷爷的爷爷一辈,为躲避战乱迁到了江苏启东这块土地上。这里靠江倚海,土壤肥沃,处于长江三角洲最东边,但南北往来商客甚少,虽离上海不过一江之隔,但行船有大风大浪的危险,一般少有人渡江过来。
在大多数人流离失所的那些年,启东地偏于一隅,过得怡然自得。经过几代人的勤奋,周家砌起了青砖瓦房,筑起了三进小院,勤快又巧手的爷爷们架起了雕花拨步大床,他们有的是办法从江那边运来各种在南方的名贵木材、青砖石材等。这种精致又繁盛的院落,即使在文革以后,小小的我也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细腻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热情。
福兮祸所依、祸兮福所伏。在我外祖父4岁的时候,一场疫情席卷了整个村落。据外祖父的说法,人们传染式的腹泻、头痛、发烧、寒战,随之死亡便到来。
解放前,医疗水平落后,受到传染性疾病威胁的群众只能自发性的活者隔离、死者焚烧。短短一个月内,周家竟只剩外曾祖父和年幼的外祖父两人,外祖父的母亲和2个手足兄弟也无一幸免。村人虽可怜独苗,但求自保躲避不及,皆嘘周家独苗熬不过几日而已。
也仅几日,外祖父也开始恶疾发作,高烧昏迷不醒,村人皆不敢靠前。此时,唯村中汤家送来米水渡入外祖父口中续命。见村人只等幼儿断气收尸,外曾祖父跺脚眼泪直流,暗中与汤家商定,一日趁着夜色将外祖父送到了汤家。此日后,村人皆绕汤家而行,一些凶悍的村民严令汤家不准一人外出与人接触。在汤家内屋隔离半月后,外祖父竟渐有起色,三个月后回到周家宅子,开始发愤图强、重振家业。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既演绎着兴盛与衰败,也碾压着一个民族和旧社会人们沉重的喘息。一声夹杂着血肉的巨响,日机的轰炸又打破了一度平静的生活。
据外祖父讲,那时沙下人一缸盐能换沙上人一缸海蜇,我想这跟新疆当年村民一袋蔬菜能换牧民一只羊是一样的概念吧!当日,正在吕四镇换海蜇的外祖父听到日本飞机的声音,扭头就见飞机从头上掠过,可以清楚的看到日本飞行员的钢盔,人们恐慌的聚集奔跑,日军竟紧赶着聚集奔跑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进行投弹轰炸,外祖父蹲在集市一角悲愤地目睹了日军的暴行。由于当天炸死的人较多,一时之间,吕四镇到处是呼唤亲人的悲呼声,数百住宅被毁,平民无家可归,繁华的街市陷入了一片凄凉之中。
外祖父回去后,便倾家中所有财物,全数交予当地的义勇军用来抗日,并四处游说村人保国才能保家。外曾祖父则时常往来沙家滨办事,回来常跟外祖父夸赞阿庆嫂夫妇俩的聪明机智,所以我们后人判断当时外曾祖父是在为新四军办事。有一日,正当大年除夕夜,驻扎当地的日军进村扫荡,外祖父全家丢下碗筷扑门而出藏到村后的坟茔中,怀中抱着尚在襁褓中的两个孩子,也就是我大舅和二舅,竟在漆黑莫辨的寒风中没有哭闹一声,侥幸逃过一劫。
解放后,历经磨难的外祖父这代人,终于得到修养生息。外祖父凭借一手好字和巧工谋得了生计,5个孩子也开始识字学文。但生活的磨难与考验并没有结束,随后到来的自然灾害和饥荒,迫使外祖父与外祖母忍痛将二女儿也就是我母亲送人抚养,只为家里省出一份粮来,使送养的孩子和留下的孩子都能多一份生的希望。
在这样时日维艰的境况下,我的外祖母江宝英还做了一件善事。
有一天清晨,家门口来了一个江北小娘子,身后还背了一个瘦弱的孩子,手里拿了个瘪荡荡的布袋讨要吃的,一看就是走了很多路、饿了很久。
当时我的外祖母出于本能,面对围坐在桌前饿的嗷嗷叫唤的子女们,居然毫不犹豫的从桌上照得见人影的米汤里舀起底下最厚的一层,送到江北小娘子手中,帮她喂起了孩子,走的时候还盛了半瓢米装到小娘子的布袋里。小娘子千恩万谢走了,全家人却陷入到沉重的恐慌中,不知明日拿什么填饱一家人的肚子!后来整整隔了十年,这位住在秦潭的江北小娘子为这半瓢米寻回来感谢我的外祖母,两家交好常来常往,一时又成美谈。
思忆周家世代沉浮,那斑驳陈旧的木门上,先人留下的“不求金玉贵、但求子孙贤”的祖训,后人代代谨遵。回想幼时与外祖父、外祖母相处的场景,他们的一言一行养成了我一生的习惯,他们每一个平凡的心愿都成为了我毕生追求的信念。
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里,祖祖辈辈怀着对美好生活不懈的追求,与天争与地斗、忘我勤奋劳作,就是为了让下一代人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。经历血与火的洗礼,饥饿与疾病的磨难,仍绵延不绝、生生不息。
从汤家的一碗米汤到外祖母赠人的米汤到今天的构筑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,这正是泱泱大国民众的共同心声;从旧社会疫病中垂死挣扎的幼儿到新中国“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”,无数个“舍小家,顾大家”的英雄与勇士不计生死冲在疫情一线,这正是中华民族大义精神的延续!
如今,14亿民众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,抗击疫情!明日,春暖花开后,我们这一代人更应激浊扬清、同舟共济、发奋图强为共建大美中华加砖添瓦!(且末县纪委监委 季解放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