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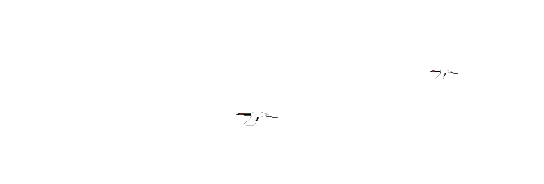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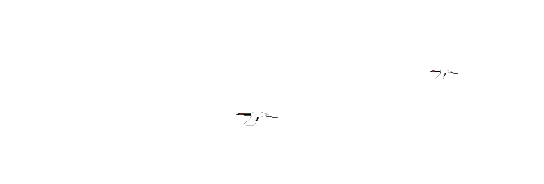

磁州窑贾逵勤学瓷枕。

南宋刻本《后汉书·郑范陈贾张列传》书影,其中“贾”指的是贾逵。 资料图片

磁州窑时苗留犊瓷枕。资料图片
磁州窑赵抃入蜀瓷枕。资料图片
瓷枕是古人日用之物,具有消暑降温的功效。古人巧妙构思瓷枕的造型,在瓷枕上精心绘制图案,有梅兰竹菊、戏曲故事、文人墨客、清官廉吏等,请欣赏三方河北邯郸磁州窑制造的瓷枕,了解其中蕴含的廉洁故事、家风故事。
贾逵勤学
北宋诗人张耒是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,苏轼称赞他的文章“汪洋冲澹,有一唱三叹之声”。张耒的一位朋友,赠其一方瓷枕,张耒以诗为谢,写道:“巩人作枕坚且青,故人赠我消炎蒸。持之入室凉风生,脑寒发冷泥丸惊。”这瓷枕有消暑降温的功效,诗人不无夸张地说,将瓷枕拿到室内,仿佛一阵凉风吹入,枕上瓷枕,不仅发丝感到清凉,那凉意直冲天灵盖,令人惊醒。
瓷枕不仅具有实用价值,也具有美学价值,其造型、颜色、装饰图案体现出古代匠人的精巧构思。我国古代生产瓷枕的窑系众多,河北邯郸磁州窑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。它从北朝创烧,一直延续至明清时代,而以宋金元时代最为繁荣。磁州窑的窑址,目前在河北省邯郸市磁县、峰峰矿区发现多处,这些地方为古磁州之地,故名磁州窑。
磁州窑是民间窑场,以生产百姓日用瓷器为主,或许并不如官窑生产的瓷器那么精致,却处处展现出活泼的生气。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花、黑釉白花的瓷器而知名,在颜色上对比鲜明、浓烈大方,擅长使用剔刻的技法在瓷器表面刻出纹饰。
位于峰峰矿区的磁州窑艺术馆,收藏了一件元代“贾逵勤学”瓷枕,讲述了一位东汉大儒的故事。该瓷枕在白色釉面上,用黑色线条绘制出人物与纹饰,线条流畅简率、不事雕琢。枕面菱花形开光内,绘制出一个庭院内有石头和树木,一间小小的学堂中,老师在书桌后坐着,两位学生正在向老师请教问题,学堂门口,两位学生正向来访者作揖行礼。来访者共有三位,母亲带着孩子走在前方,父亲肩挑扁担跟在后头,扁担上装着的或许就是给老师的“束脩”,他们要将孩子送去学堂读书。
学堂中的老师就是贾逵。东晋学者王嘉的名下有一部著名笔记《拾遗记》,说贾逵“经史遍通”,乡里人都对他很尊敬,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学问的人。他在乡里开设学堂收徒,有不远万里来求学者,更有甚者,带着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孩子,在贾逵家旁住下来,就为能得到贾逵的指点。
因为前来求学的人众多,他们向老师赠送的粮食,都能装满一个小粮仓。有人对此评价“贾逵非力耕所得,诵经舌倦,世所谓舌耕也”。后世遂将教书谋生称为“舌耕”。
贾逵通过勤奋读书,终成一代大儒。他的成长之路上,离不开姐姐的帮助。王嘉的书中说贾逵的姐姐“以贞明见称”。贾逵年幼时,她听到邻居家有人在读书,就抱着贾逵隔着篱笆听,贾逵“静听不言”,姐姐大喜,认为弟弟是读书种子。贾逵十岁时,已能“暗诵六经”,这让姐姐觉得很是意外,她问弟弟自家因为贫困,不曾请人上门授课,你如何知道有这些经典,且能背诵出来呢?贾逵说:“忆昔姊抱逵于篱间,听邻家读书,今万不遗一。”为了更好地记诵,贾逵将自己记忆中的经典写下来,或写在庭中的桑叶上,或直接写在门扉上。
其实,从正史的记载看,贾逵学习儒家经典,更多的是继承了家学。他的父亲贾徽曾经拜师刘歆学习《春秋左氏传》,“兼习《国语》《周官》”,日后贾逵也是以治《春秋左氏传》而扬名天下。
贾逵还曾进入太学读书,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说他在太学读书时,一心扑在读书上,喜欢问问题,因为他个头比较大,同学们说他“问事不休贾长头”。贾逵还曾与班固一起整理宫廷藏书。
尽管笔记与正史对贾逵的记载有出入,但通过这方瓷枕,我们得以知道民间更喜欢笔记中贾逵勤学的故事,这个故事更加生动、有趣,也更打动人心,它反映了民间对于读书学习的高度重视,相信勤学能改变自己的命运,也能改变家族的命运。
时苗留犊
国家一级博物馆邯郸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元代磁州窑“时苗留犊”瓷枕。它与“贾逵勤学”瓷枕形制相同,菱花形开光内绘有两株茂盛的松树。松树下有一辆牛车,车夫站在车旁,等待着时苗和夫人上车。车尾,时苗和夫人正与三位前来送行的百姓依依惜别,送行者手中捧物,要送给时苗,时苗做推辞状。三位送行者身后,还有一人牵着一头小牛前来。
时苗是河北巨鹿人,生活年代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代。史籍说他“少清白,为人疾恶”,清白廉洁、嫉恶如仇。他曾任安徽寿春(今安徽淮南寿县)县令,“时苗留犊”的故事就发生在他寿春任上。赴任时,他乘着一辆牛车而来,牛在寿春生下了牛犊。离任时,时苗对同僚说:“令来时本无此犊,犊是淮南所生有也”,要将牛犊留在寿春。同僚劝道“六畜不识父,自当随母”,主张让时苗带着牛犊走,但最终时苗坚持留下牛犊。《寿县志》说时苗“教民有法,平昔以廉守自儆”,直至今日,寿县还有一座纪念时苗的时公祠。
史籍中关于时苗的记载非常有限,然而留犊一事不仅使时苗当时就“名闻天下”,更得到后来人们的不断赞颂。元代学者王恽有一首《题时苗留犊》:“清白居官志不贪,故教留犊在淮南。时人莫作沽名诮,千载何曾见二三。”针对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时苗留犊有沽名钓誉之嫌,王恽在诗中说不必以此讥笑时苗,这正是他“清白居官”的表现,这样自律极严的清官,历史上可是不多见。
元代画家钱选绘有《时苗留犊图》,可见这一题材在元代很受欢迎,不仅文人画家喜欢,民间瓷工也喜欢。
官员离任留下什么、带走什么,时苗留犊做出了示范。明代冯梦龙的《广笑府》中,说有一个贪官离任时,将府库“席卷一空”,百姓送给他一块“德政匾”,只见上面是一首讽刺诗:“来时萧索去时丰,官帑民财一扫空。只有江山移不去,临行写入画图中。”若是当地的山山水水也能带走,恐怕也会被其“席卷一空”,与时苗留犊相比,真有天壤之别。
一琴一鹤
位于磁县的磁州窑博物馆,藏有一金代赵抃入蜀图长方枕,菱花形开光内绘制出一策杖前行的老者,他的身后跟随着一位怀抱古琴的童仆,老者前方有一龟、一鹤,俱引颈向上,龟吐云气,鹤在长鸣。
这位老者就是北宋有“铁面御史”美称的赵抃,他任殿中侍御史时,“弹劾不避权倖,声称凛然”,但为品格高尚的“正人端士”,他敢于挺身而出,为他们辩护。欧阳修等人自请外放,赵抃向朝廷进言,欧阳修等人不仅才华出众,而且“正色立朝,不能谄事权要”,这样的人才应留在朝中任职,欧阳修等人由此得留。
赵抃与四川有着深厚缘分,他曾四次入蜀、五任蜀职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提到,赵抃任成都转运使时,“出行部内,唯携一琴一鹤,坐则看鹤鼓琴”,他曾过青城山,正赶上天降大雪,不得不借宿旅舍一夜,有旅客不知他的身份,轻慢于他,“公(指赵抃)颓然鼓琴不问”。
琴、鹤乃古代文士珍爱之物,其雅洁、清高契合文士的审美趣味、人格理想。赵抃将琴、鹤当成知己,亦将百姓福祉记挂在心间。
宋英宗治平元年(1064),赵抃以龙图阁直学士、吏部员外郎知成都府,此番来蜀,他“以宽为治”。针对“聚为妖祀者”,赵抃此前曾用“峻法”整治,这次到任后,又有妖祀案发生,蜀民皆认为参与其中的人难逃责罚,不免担惊受怕。经过调查后,赵抃认为此案并未造成重大影响,“是特酒食过耳”,是宴饮过度导致的,“刑首恶而释余人,蜀民大悦”。
宋神宗即位后,任命赵抃知谏院,他亦知其“一琴一鹤入西蜀”的故事,对赵抃说:“闻卿匹马入蜀,以一琴一鹤自随,为政简易,亦称是乎?”宋神宗认为赵抃的性格之简与为政之简是相称的。宋神宗熙宁五年(1072),赵抃以资政殿大学士复知成都,“既至蜀,治益尚宽”。他曾勉励堂下与自己年岁相当的老吏,“汝亦宜清谨畏戢以帅众”,以清白、谨慎、敬畏、内敛处事,给其他吏员做个榜样。
史载,赵抃初入蜀时,经过了一条水质洁净的大江,他指江水为誓:“吾志如此江清白,虽万类混淆其中,不少浊也。”后来,人们便将此江称为青白江。赵抃的清廉故事,不仅写在流传千年的器物上,也写入了山河地理中。(陈彧之)